——《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书稿完成
李尚勇
(一)
今天,我为书稿《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曙光——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第8稿(定稿)写下了最后一个字。当我为书稿插入定稿日期时才发现,今天居然是“5.12”汶川大地震8周年纪念日,笔者对地震预报制度的研究及本书写作历时正好8年整。于是,欣然“提笔”写下了如下文字。(这不是笔者刻意安排的“巧合”,因为原定第8稿的完稿日期一再推迟,才撞上了这个日子——这是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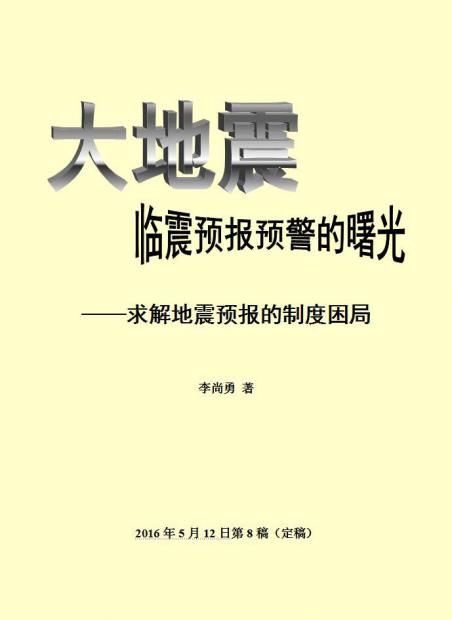
本书的“内容提要”可以概括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情况,我也就不再另行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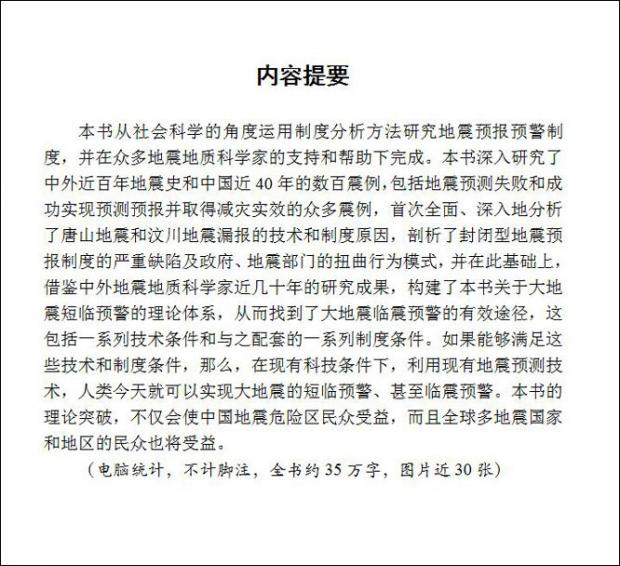
笔者不是地震专家,但碰巧有理工科背景,因而能够理解地震预测预报的科技和制度问题。本书并不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评析地震预测预报的功过是非;笔者是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首次尝试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用制度研究方法去分析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从昔日辉煌坠落并陷入困局的制度原因。
8年来,受益于众多地震地质科学家和地震专家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笔者得以完成这一研究并完成书稿写作。(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本书出版时,我将一一致谢。)
一位地震学家(长期在国家地震局从事地震预测工作并担任部门领导,请原谅,我目前还不能披露他的姓名和职务)在看过本书第7稿后评论说:“你,作为一个原先地震预报的‘局外人’,肯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去研究地震预报问题,不仅探讨了地震预报工作存在的问题,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设想,所涉及知识之广,研究问题深入之程度是我们这些‘局内人’深感不及的。在此,我除以一个老地震工作者的名义向你表达深切的敬意和谢意外,就是对本书涉及的人和事,尽我所知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你。”
在几位高层次地震地质科学家的帮助下,本书第8稿因为新增了许多珍贵史料而更接近我国地震预报的历史真实。受益于笔者构建的理论体系和来源可靠的史料,本书第一次披露了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漏报的那些关键性技术和历史细节。
(二)
大地震关乎成千成万民众的生命安全,而汶川大地震以来,一系列大地震漏报,民众伤亡惨重,这包括,2008年“5.12”四川汶川8.0级地震,87150人震亡失踪;2010年“4.14”青海玉树7.2级地震,2968人震亡失踪;2013年“4.20”四川芦山7.0级地震,217人震亡失踪,2014年“8.3”云南鲁甸6.5级地震,729人震亡失踪。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75—1976年,地方政府发布了5个大地震临震预报,取得了相当大的减灾实效。这包括1975年的海城7.3级地震(震亡1328人,占受灾区总人口的0.016%),1976年的云南龙陵7.3、7.4级地震(仅有98人震亡)、唐山7.8级地震中的“青龙奇迹”(河北青龙县因发布临震预报无一人震亡)、四川松潘平武7.2级双震(仅有38人震亡)和四川盐源云南宁蒗6.7级地震(仅有33人震亡)。
1976年全年,全国共发生了6个6级以上地震,除了内蒙古2个6.2级地震没有预报(当时缺少监测力量)以外,云南、河北(青龙)、四川等地4个6.7~7.8级大地震,都成功发布了临震预报,取得了相当出色的减灾实效。这显然不能用“偶然成功”来解释。
2010年“4.
然而,根据本书的研究,要想实现上述工作目标,只有改革我国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一条路。这是因为,(1)因为片面盲目地追求现代化、数字化、与国际接轨,并走上了专业化、学术化、职务化、官僚化的道路,以地震部门为主的“主流预测”越来越没有大地震短临预测(尤其是临震预测)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他们大肆宣扬“地震不能预报”,以便为下一次大地震漏报预留“后门”。(2)若没有与“主流预测”合作的制度平台,以非在职、非在岗的地震地质科学家和民间地震预测专家为主的“非主流预测”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中强地震的短期和临震预测,但是,几乎所有正确的短临预测都不可能为“主流预测”所接受,各级政府也不可能依据个别“非主流预测”的临震预测发布临震预报。这就是这些年来,“非主流预测”不断有正确的短临预测,但完全没有减灾实效的根本原因。
本书关于大地震短临预警的理论体系、关于大地震临震预警的有效途径,包括一系列技术条件和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条件,而这“一系列制度条件”的形成只能以“改革我国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为前提。
通过这一体制改革整合我国的地震预测力量,形成各种预测力量全面合作的制度平台,这一制度平台能够容纳并促进主流预测与非主流预测、主流非主流预测与群测群防,以及专业预测与地震危险区广大群众之间的相互合作。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制定的上述工作目标才可能现实,各种预测力量所形成的大地震短临预测(尤其是临震预测),才能够转化为真实的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而“非主流预测”的正确短期和临震预测才可能产生减灾实效,受大地震威胁的民众才能够真正受益。
(三)
下面是本书的最后一节(第10章第六节)“开放型地震预测预警制度试点”:
在全国全面实行开放型地震预测预警制度,不仅会对传统地震预报体制及其观念带来很大冲击,而且还会引发相关利益调整,因此,推行并实施新体制的阻力会很大。根据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如此重大的利益调整前,需要先行试点,只有在试点中取得制度组织经验并产生明显的减灾实效后,即“大地震临震预警的有效途径”及本书的理论体系得到到实践检验后,全面推广开放型制度才会产生水到渠成的效果。
鉴于此,笔者建议,可在近期划定的地震重点危险区中,挑选2、3个县进行开放型制度试点;依目前全国震情形势,试点候选地点宜选择在“鲜水河断裂带—安宁河断裂带”及其附近地区。
近10年,鲜水河断裂带和安宁河断裂带一直是国家地震局重点关注的大地震危险区;近两年,处于鲜水河断裂带、安宁河断裂带和龙门山断裂带所构成的“Y”字型构造带地区的一些市州区县多次遭遇由主流预测(地震部门)内部通报的“短期紧急震情”。
在这一“Y”字型构造带地区,地震地质环境异常复杂。李有才和吴玉宝等地震地质专家的研究显示,“该地区是多组活动性很强的断裂带相交汇的脆弱地带,该地区具有发生类似汶川8.0级大地震的地质构造环境”。
在这个“Y”字型构造带地区,大渡河不到
面对如此情形,与2002年一样,李有才再次质疑地震部门的“历史—概率法”及其结论,并用3年时间再次用“确定性方法”分析了该地区的地震危险性。鉴于这一地区的大地震孕震背景和近期一再出现中短期震情,笔者与李有才合作,于2013年底撰写了内参报告。2014年4月,该报告以《高度重视瀑布沟水库地震安全形势》为题,通过人民日报《内参》(2014年第31期),呈送中央领导。稍后,该报告由中央领导批转国家地震局;同年5月,该局在成都为我俩召开了“瀑布沟地区地质构造专题研讨会”。与2003年“威胁、恐吓”李有才的那个“座谈会”(参见第8章第1节)相比,这个“研讨会”有了很大进步。这一次,国家地震局官员和专家态度和蔼,用语谦虚,虽学术争论气氛很浓,但没有出现“紧张气氛”。研讨会自始至终具有“建设性”性质。(后来得知,会后有关部门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再次“打地钉”加固新县城山岩,一个是全面排查省内水库安全。)
其实,笔者与李有才的本意不是要讨论库坝区的地质问题,因为特大型水电工程已成事实,无可改变,我们是希望高层关注该地区严峻的地震形势,“警惕瀑布沟水库成为紫坪铺水库第二”,并在此“进行开放型地震预测预警制度试点”,最大限度减少可能的人员伤亡。
笔者当时提出的建议是:(1)按照笔者2013年给中央领导的建议,在该地区进行“开放型地震预测预警制度试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小型的主流、非主流两支地震预测力量合作的制度平台,专门处理该地区的地震预测预警信息。(2)全面启动该地区群测群防工作,广泛动员当地群众积极参与,并建立起有如当年海城和唐山地区那样的群测群防监测网,为上述合作平台及时提供地震微观和宏观异常信息。(3)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地震学家和专家以及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将他们比较成熟的地震前兆异常监测仪器安装布置在试点地区,允许他们将这个地区作为地震短临预测的试验场。
在秦四清(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研究员)的理论体系中,鲜水河断裂带和安宁河断裂带分别被划为鲜水河地震区和西昌地震区。对这两个地震区,秦四清研究团队一直保持高度警觉,并在2010—2015年的多篇论文中多次进行了中长期预测,基本结论均是,“将会发生MS7.5级以上地震,且已经非常接近临界状态”。
2015年10月,秦四清根据最新数据,作出了最新的中长期预测,结论是,这2个7、8级地震距离我们更近了。(参见:秦四清的《鲜水河、西昌与得荣地震区目前的态势》,科学网/秦四清的博文,
由于这两个地震区相互依靠,未来2个大地震的震中位置也很近,再加上邻近的得荣地震区MS7.4~7.7级地震已处于临界状态(中短期预测),所以,笔者认为,不排除一个大震提前诱发另外一个或两个大震,从而形成“连环大震”的可能性。
可见,主流预测和非主流预测这一次对地震趋势的认识高度一致,上述“Y”字型构造带地区地震形势相当严峻,短期性质的“冲击”一再出现,大地震的脚步声“嗒嗒”作响,因此,选择该地区进行“开放型地震预测预警制度”试点不仅必要,而且显得很紧迫。
反之,如果没有如此“试点”这样一个契机,那么,这一片已经接近临界状态的地震重点危险区的大震(或连环大震),极有可能再度重演大地震漏报的人间悲剧!
【友情提示】本书谋求正式出版,只有这样才可能为“改革我国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出力。本书拟出版中文简体、中文繁体和非中文语种各版本。敬请中外出版界的朋友、有外文翻译出版能力的朋友与笔者联系,敬请网友将本书推荐给你所认识的出版社编辑,或者有外文翻译能力的朋友。谢谢!(联系邮箱:)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